這些發生在美國的真實案例,有的是因為罹患癌症、愛滋病等疾病,有的則是因為用藥不當或車禍等意外而導致失去行為能力的病人。由於當時(大約 1970 年之前)醫界與一般民眾對於安寧療護、疼痛控制的認知還相當貧乏,對臨終病人與家屬能否決定拔管(呼吸器、鼻胃管)也存在歧見,使得那些重症病患在往生的前幾個月,不僅自己痛苦,家人也承受了極大的身心煎熬;有的家屬甚至奮戰近十年,與各種團體和政治勢力對抗,才促使美國政府制定相關法令,包括預立醫囑的合法性、將「全腦功能停止」納入死亡的定義(原本僅有心肺、呼吸功能停止)。作者透過採訪當事人所作的記錄,如實呈現臨終病人的心理變化與種種痛苦,同時對安寧療護、使用止痛藥與麻醉劑來控制疼痛的劑量如何才算適當、醫生的權威、病人與家屬自決的權利、安樂死等牽涉道德與法律層面的問題也多有探討。這才發現,原來這當中牽涉的問題是如此複雜:當我躺在病床上無法表達意見時,誰來決定我的生死?何時才應該放棄維持器官運作的治療?萬一還有一線生機呢?誰來執行(醫生也會擔心被告)?病人或家屬有權利不斷提高止痛藥的劑量嗎?
安詳離世:茱迪絲的旅程
書中的第一個案例,茱迪絲,因罹患乳癌而切除乳房,中間歷經數次化療和放射線治療,也試過各種非正統的醫療方法,如禪修冥想、印地安巫醫的召喚聖靈療法等(人到無可奈何時總會求助各種偏方),最終仍不幸離世。幸運的是,她最後選擇了與勇敢面對死亡,放棄進一步治療,而在家中與親人共同度過最後一段寧靜而美好的時光。就如茱迪絲的丈夫所說:
「很顯然,我的妻子過世了,但對我們所有人來說,她死去的方式是那麼強而有力、獨特非凡。它讓我體悟到,死亡是一段旅程,而茱迪絲的旅程是美好的。......我唯一能說的是,對於我、賈斯汀和希瑟莉而言,茱迪絲的死讓我們深覺自己何其有幸,也何其不幸。」
現代醫學訓練教些什麼?
作者在第二章討論了一些醫病關係與醫學倫理的議題。例如她提到,原本死亡是人生的最終結果,但是在醫生的手中死亡,卻似乎成了醫生的失敗或過失。「因此之故,教學醫院訓練年輕醫師不顧成功機率的多寡,盡可能去嘗試每一種賭博。他們一次只把焦點放在一個器官上,專科醫師的狹窄見識使他們不去質疑,一個經過修復的心臟,能否與一個受損的肺臟一起正常運作;或者,對於一個纏綿病榻、承受極大痛楚的人,或肺臟、腎臟衰竭的人來說,修復修臟有什麼幫助?」(p. 76)
原來,醫學技術的進步,不止延長了人的生命,也同時延長了病人的痛苦,以致於在這個國家,「死亡竟是如此艱難」。
艱難的休止符:只想從疼痛中解脫
第二個案例,彼得,是一名罹患愛滋病的同性戀者。當時(1986 年),人們對愛滋病幾乎一無所知,對愛滋病所引發的各種疼痛,包括頭痛、腹部絞痛、以及最棘手的神經病變引發的疼痛,也鮮少有醫生知道該如何給予適當的治療。經過一段時間,彼得終於認清自己的處境,有一天,他對他的伴侶朗恩說:「嘿,這病是一天天節節進逼。它現在在我的脊椎裡,一路往上進攻,等到它攻進橫膈膜,我就一命嗚呼了。朗恩,我們得談一談。我再也不想回醫院去了。」
彼得後來如願進入安寧病院(hospice)。剛開始,病院的醫師准許彼得日以繼夜的服用口服嗎啡,彼得總算有一段比較輕鬆的日子。但是到後來,疼痛愈加劇烈,他一而再,再而三的索求止痛藥,連護士和醫生都已經厭煩他的「討藥」行為,認為他對嗎啡已經上癮了,甚至有無病呻吟的嫌疑。朗恩回憶:
「當我坐在床邊,陪伴逐漸油盡燈枯的彼得時,聽到他一再懇請、拜託、哀求醫護人員給他更多嗎啡--即使當時已經每小時靜脈注射四十或五十毫克的嗎啡溶液--直到他再也無法言語為止。即使在那個時候,我還是聽到醫護人員說不。彼得終於放棄希望,不再哀求。當他呻吟時,我撫摸他的額頭,當他嘆息時,我握住他的手。他的疼痛似乎未曾稍停,除了生命終了的最後時刻。」(p.109)
真的是痛到死!
彼得過世後,當時負責治療他的醫生反問:「何謂適當醫療?難道是指醫師隨著病人的意思照辦嗎?還是讓病人服用麻醉藥物到飄飄欲仙?如果這才叫作適當的醫療,何必浪費良藥?......我們遇到一些病人要求高劑量的藥物,因為他們一心想死。我們不幫助病人安樂死。」
另一位醫生持不同看法:「對於一個垂死的愛滋病人而言,每小時五十毫克的靜脈注射嗎啡通常是不夠的。所謂足夠,乃是指舒解病人疼痛的劑量。『相信病人』是良醫良藥的首要原則。」也就是說,疼痛是主觀的,病人喊痛就是痛,應盡量給予治療。若懷疑病人過度索求止痛藥而不給予治療,這樣的醫師......病人碰到了恐怕只能自求多福。
到底該不該拔管?
第三個案例,凱倫,一個昏迷十年之後才過世的年輕女孩,她的父母為了讓她早日脫離人間煉獄,不惜和醫院打官司。而凱倫在生日時向朋友吐露的心聲,竟成為日後打官司時有力的證詞。當時,凱倫對朋友表示,如果有一天她回天乏術,活著只會延長痛苦折磨,她寧願死。
儘管美國最高法院最後判定醫院應依照凱倫父母的意願,拔除凱倫的人工呼吸器。但醫師還是不肯照做,只願意採用逐漸讓凱倫試著不依賴人工呼吸器一段時間的方式。結果等到正式將人工呼吸器關機時,凱倫卻奇蹟式的能夠自行呼吸了。這個「好消息」讓凱倫和家人陷入更長的磨難,直到昏迷十年後才得以解脫。
「醫師指出,事實上,當餵食管或靜脈注射點滴被移除,或停止洗腎,死亡就不那麼可怕或痛苦。如果能夠妥善控制,拔除所有的插管,身體將慢慢地停止運作,自然而然地進入自我麻醉的睡眠狀態,病人便能平靜安詳地死亡。」(p.162)
病人自決
在凱倫的案例中,法院後來雖然允許其父母拔除凱倫的餵食管,但他們卻一直沒有這麼做。而本書第四個案例的主角--南西--卻在其父母欲拔除其鼻胃管時引發激烈爭議。甚至有牧師帶頭策劃「營救行動」,欲強行進入醫院幫南西重新插上鼻胃管。他們的標語是「你想嚐嚐被餓死的滋味嗎?」「當所有美國人在聖誕節前大祭五臟廟,南西卻活活挨餓,脫水至死。」
歷經宗教團體、醫界、反墮胎委員會等各方政治角力,南西的鼻胃管終究被拔除了。而這些爭議也催生了各種臨終法的制定,包括「生前遺囑」、「醫療委任代理人委託書」、以及「家屬同意書」。這些法案的內容我並不清楚,但從字面上可大致了解,其核心概念就是要尊重病人對自己醫療方式的決定權。
這本書出版於 1999 年,距今已十個年頭,而且談的是美國的情況,不知道台灣是否有制定類似的生命臨終法案?萬一將來有一天我成了活死人,身上插滿各種管子,無法言語時,我應該也會希望盡快解脫,也免除家人的身心折磨吧。
ps. 本書已絕版,目前大概只能到圖書館或二手書店才找得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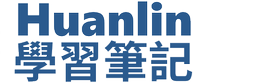

可以先把遺囑立好。這樣家人就知道意思了,不過,還是得先溝通好,以免有遺憾!推薦另一本書給你[Start the Conversation與死亡對談],也不錯!
回覆刪除好的,多謝您的建議與推薦。看來,《與死亡對談》也是得到圖書館或二手書店才找得到了。
回覆刪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