書名:地下室手記
作者:杜斯妥也夫斯基
譯者:孟祥森
出版社:印刻
出版日期:2003 年 1 月
這本書一個有趣的地方,就是神經質的獨白和假想的對話,以下摘錄部分內容。
書摘:
各位先生,我請你們找個時間去聽聽十九世紀有教養的人牙痛時發出的呻吟,聽聽在牙痛的第二天開始發出的呻吟。意即是說,不像第一天那樣,不僅是因為牙痛而發出......他的呻吟骯髒可厭的帶著惡意,並且日日夜夜繼續下去。他自己當然知道這種呻吟對自己毫無益處,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是在毫無道理的折磨別人和他自己。他的家人,完全帶著一種厭惡在聽他,他們一點也不相信他真正需要這種呻吟,他們心裡都知道他可以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,更為單純的,不要尖叫,不要揮拳踢腿;他們都知道他現在這種呻吟僅僅是為了取樂自己,是出於情緒不良,是出於惡意。(p.19)
註:尊貴的上流社會人士,牙痛時也是一樣的哀嚎,甚至唉得更難聽。有些已經不是單純因為疼痛而哀嚎,其中帶有刻意(惡意?)的成分。
「哈,哈,但是你知道實際上根本沒有甚麼叫做選擇的東西,不管你怎麼說」你會咯格笑著打斷我。「科學對於人的分析已經到達如此的程度,以致我們老早知道所謂選擇和自由意志僅不過是--」
住口!先生,這個話讓我自己說。 (p.36)
註:叫自己想像的人住口 :)
我寫它的目的是什麼?如果我不是為了給別人看,我何必把這些偶然的事情寫在紙上,而不僅僅是心裡想想就算了?
完全對;但是,寫在紙上比較神氣。寫在紙上有一個重要的意義:我可以評論一下自己,我可以改善我的文體。此外,由於把它寫出來,我或許實際上可以使自己輕鬆一下。(p.56)
由於我無限制的虛榮心,由於我為自己所訂下的過高的標準,我時常以極不滿意的眼光看待自己,幾乎已經到達厭惡的程度,於是內心裡我認為每個人對我都有這種感覺。 (p.60)
一個有教養、莊重的人不可能不給自己定下可怕的崇高標準,有些時候不可能不鄙視自己甚至憎恨自己。然而不論我鄙視他們或覺得他們比我強,每次我遇到任何人,總是把眼睛低下來。我甚至做過好多次實驗,看看我能不能面對面直視著別人,但我總是第一個把眼睛低下來。這幾乎使我煩惱得神經錯亂。......我根本是個病態敏感的人--像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必然會成為這個樣子。(p.60-61)
註:宅男必練基本功:兩眼直視對方,看誰先躲開視線。
絕大部分時間我都留在家裡,看書。我試圖用外來的力量窒息一切不斷在我心中滋擾的東西。而我所具有的唯一方法就是讀書。當然,讀書給我很大的幫助--使我激動、快樂或痛苦。但有些時候它使我感到可怕的厭倦。那時候我甚麼都不想,只想活動活動,於是,我投入黑暗的,地下室的,最可厭最卑下的罪惡之中。我那不幸的熱情是銳利的、惱人的,是由我不斷的、病態的易怒性格產生出來的。......除了讀書之外我沒有任何消遣;這是說,我週遭的一切沒有一件東西使我尊敬,沒有一件東西吸引我。同樣,我被沮喪壓得透不過氣來;我神經質的渴望衝突和矛盾,因此我喜歡罪惡。我說這話並不是要證明自己有道理......不,我在說謊......我就是要證明自己有道理。我說這話完全是為了對自己有好處,先生,我不要說謊。我發誓不說謊。
於是,到了晚上,我偷偷摸摸的,膽卻的,孤獨的縱情在那種骯髒的罪惡中,心裡從未離開過羞恥感;這種羞恥感即使在最可憎的時刻都不曾離開我,以致使我對它咒罵。在那個時候我心裡就早有了地下室,我極端懼怕被人闖見,被人認出來。 (p.66)
註: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地下室?
有一個軍官推我......我可以原諒別人用拳頭揍我,卻絕不能原諒把我推開而竟然沒有注意到我。....請你不要以為我躲避那個軍官是出於懦弱:我內心裡永遠不曾懦弱過,雖然我的行為總是使我成為一個懦夫。你別忙著笑--我可以保證能夠向你解釋。
......我躲開他並不是由於懦弱,而是由於無限的虛榮心。......我害怕的是在場的每個人......當我開始反抗並用斯文的語言爭辯的時候,他們都要開始嘲笑我,不瞭解我。
註:寧願被揍也不要被人忽視,欲找人尋仇把面子討回來,卻又怕被其他人嘲笑。下文有點長,故未摘錄,大意是他還是老想著討回面子,於是跟蹤那軍官好幾次,要查他的底細和幹過的齷齪事,最後還寫了封非常漂亮的決鬥信,向那名軍官下戰帖。結果這封信並未寄出,而他也因為沒有寄出這封信而感謝上帝,因為,每當他想到把信送給軍官的後果時,他就感到「有一股寒流通過背脊」,同時宣稱「我用最簡單的方式為自己復了仇,這完全是天才手法!」呵,還真天才。
有些假日,我經常沿著涅夫斯基大道有陽光的一邊散步......實際上不能說是散步,因為總有這麼多不愉快的屈辱與怨恨發生;但無疑地,這正是我想要的。我總是穿著最不像樣的服裝沿路蠕動,像一條鱔魚,隨時給將軍,騎兵軍官或女士們讓路,在這時候我心裡常常感到絞痛。......在全世界的眼睛裡我只是一隻蒼蠅,一隻骯髒的、可厭的蒼蠅。--當然,我比所有這些人都更聰明,心靈有更高度的發展,情感更為敏銳......為什麼我要去涅夫斯基?我不知道。我只覺得只要有機會我就被吸到那裡去。
註:精神被虐狂?自認比別人更聰明、高尚,又覺得別人都瞧不起自己,可是卻又不由自主的老是往人群裡擠,讓自己感受那精神上的屈辱與折磨。另外,這用鱔魚來形容一個人猥瑣的行走模樣,在《高老頭》裡面也有:「胖子西爾維立即上來報告女主人,說有個漂亮得不像良家婦女的姑娘,裝扮得神仙似的,穿著一雙毫無灰土的薄底呢靴,像鰻魚一樣從街上一直溜進廚房,問高里奧先生的房間在哪兒。」真是生動有趣的比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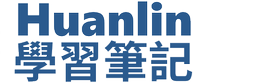

沒有留言: